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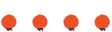

文/文 猛
这个春天,那个说起来有些拗口的疫情让我隔离家中,我有了太多的时间伫目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长江边。疫情防控的通告让长江上没有了昔日的百舸争流,但我发现依然还有船在穿行。仔细一看,船上有“万州水域环卫”的标识,除了后面的编号,那些船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江洁。
说实话,守望着长江,看到波光粼粼、江鸥翻飞的水面,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三峡清漂人,他们在水中,我在岸上。
一种从没有过的创作冲动,激发我走出书房,拨通万州清漂队队长刘古军的电话。
刘古军回话,“那你得起早床,平时我们六点出船,现在是疫情防控时期,我们必须五点出船。”
“你们在哪里?”
“早上我们在清漂码头转运垃圾。白天,我们在江上。”
站在清漂码头上,仰望天空,星星点点,环绕城市的西山、南山、北山、太白岩、天生城上独具匠心的灯饰,依山而上的城市街灯,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长江三桥、万州大桥、石宝大桥、驸马大桥上的桥灯,江面上的航标灯,一方方码头上停泊的船灯,倒影江中,湖映江城,城在湖中,唯一想起的是诗人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烁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闪烁着无数的街灯……”
感谢这群清漂人,是他们引领我等候一个清晨。天空之下,大江之边,一湖灯,一湖城,一湖风,一群人,我感受着重新涌起的蓬勃朝气、黎明的喜悦。
检查口罩,测量体温,喷洒消毒水……
“疫情严峻,你们还在坚持长江清漂?”我问刘古军。
刘古军告诉我,疫情警报在中国大地上拉响,长江上所有的船只都抛锚停在了港口,清漂队不能停。
清漂队员们说,“我们就是给长江扫江的人。大街上的环卫工,会因为风霜雨雪在家休息吗?他们是大街的环卫工,我们是大江的环卫工,给城市一条干净的街,给长江一汪清清的水,这是我们的职业。”
“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六,政府考虑安全和疫情传播等多种因素,通知我们停止清漂。开始几天,大家还坐得住,等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可一看到江面上漂浮的垃圾,一想到那些江上一直停泊的船只如今装满了污水,我们格外着急,我们多次请战出船。2月19日,上级同意了我们的请战。走上清漂码头,走上清漂船,我们的心才踏实。这不是我们有多高尚,这是我们的职业和责任!为这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一条清清的长江。江清,心就清,怕什么病毒啊?”
“你们每天都这样吗?”
“习惯啦!当年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清漂设备,垃圾和污水从船上运到车上全靠肩扛手提,手累,脚累,眼累,心累,如今一条条履带把垃圾转运车上,一条条管道把污水抽到转运车上,轻松多了,我们赶上好年代啦!”
“看着这一车车垃圾和污水运走,你们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成就感?当有一天我们驾着清漂船巡游江面,水面上干干净净,垃圾舱是空的,我们悠闲地仰望着我们的城市,轻松地漫步我们的江面……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太阳出来啦!江城春天的阳光洒在阔爽的江面,金灿灿的,我的心也如这金波一样,通体明亮。
穿上黄背心,走向最大一艘清漂船江洁003号。刘古军告诉我,今天值班的有十艘船,从我们清漂码头出发,负责主江面;他们还租用了近百余艘小渔船,负责岸边附近大船无法到达的地方。
我想起了清漂队休息室墙面上有一幅字——“江清岸洁”。我突然想明白了“江”和“岸”并列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这些曾被称为桡胡子的川江渔民没有想到的,过去他们撒网江水之下,今天他们手握网兜,关注的是江面之上。
船上的助手刘松接着刘古军的话,“在咱们三峡,现在人们不再往长江扔垃圾,垃圾用船清,沿江几十家污水处理厂、江面餐馆的污水,我们每天派船去收集,这么算下来,长江上的清漂人该是多少啊!”
船离开码头,逆水而上,我突然想到这个春天那最热泪盈眶的词语:逆行!这些朴实的长江清漂人,他们不也是这个春天的逆行者吗?
茫茫的平湖江波之上,只有他们的清漂船和岸边清漂的小渔船。过去他们清漂,过往的船只会鸣笛向他们致意,今天的江面,静静的,同着岸上静静的街道。
刘古军鸣响汽笛,为自己,为大江,为城市。
一条条漂浮垃圾以“1”字形、“S”形、“U”形和我无法描绘的形状呈现在江面。那么大的船,在五十多岁的“清漂王”刘古军手下,就如一把灵巧的铁扫帚,船过之处,江面清爽,垃圾顺着履带乖乖进入垃圾舱。碰到一些粗的木棒、大的树兜,助手刘松用铁钩调整履带向上爬的方向,让他们顺从地进入垃圾舱。
垃圾舱里垃圾越来越多,春天的阳光并不都是春暖花开,阳光照着一望无际的江面,垃圾舱中的味道逐渐升腾起来,那是闷闷的、腐烂的气味,扑入口中鼻中,心里堵得难受。
刘古军看出我的表情,说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要是夏天,一盆水泼在甲板上,眨眼间就蒸发掉。一个鸡蛋放在甲板上,不一会就晒熟了啦!至于船上那个味,今天算好的了,要是捞到漂浮的动物尸体,我保证你将永远不敢上船永远不敢想船。”
我忍不住和他们聊起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话题,他们没有我想象的沉重,说大家在家中隔离,我们在船上隔离,船就是我们的家,一边隔离,一边为长江清漂,什么都不耽误。鱼儿离不开水,我们这些老渔民离开长江还叫渔民?
趁着这片水域清漂完毕,搜寻下一片水域的时候,我拿起手机给我们三个来个自拍,突然发现本来就已经黑红的我,在他们中间居然也白面书生一回,尽管大家都戴着白色的口罩,依然遮不住黑中透着红、红中透着黑的脸,我突然发现“饱经风霜”一词用在他们身上很是单薄。我们描写在高原上生活的人的脸庞爱用高原红,对这群长江边的清漂人、老船工,我想到的是长江红。
今天却是满眼长江蓝!
春雨初歇,蓝天白云在天上,碧水清波在江面,江南江北依山而建的高楼大厦,环拥这湖水,运动场一般守望着这一汪碧水。尽管因为疫情,今天的平湖格外安静,但是这汪碧水永远是城市大客厅,迎候着南来北往的巨轮和客人。
白龙滩不算滩,提起桡子使劲扳,
千万不要打晃眼,努力闯过这一关。
扳倒起,使劲扳,要把龙角来扳弯,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龙虎滩不算滩,我们力量大如天,
要将猛虎牙扳掉,要把龙角来扳弯……
川江号子从驾驶舱传出来,唱得我热血沸腾。刘古军说,每当他们完成一片水域的“漂情”,走向下一片水域,他们总会吼几段川江号子,一天不唱就心痒,就觉得浑身无劲,何况十多天隔离家中,吼上一嗓,让他们一下忘记了疫情的阴霾。
我把他们的川江号子发在朋友圈上,但愿川江号子的力量能够荡去我们心中的阴霾。
没有闯不过去的滩……
上期精彩回顾》》》
战“疫”有我 重庆作家在行动(四十一)杜春成:守住我们的家园

渝公网安备:500103020027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