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全力抗“疫”的心!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战斗中,为打赢防疫攻坚战,重庆本土作家们以笔为枪,用文学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传递真情,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隔离病房里的“大白”们
文/邓玉霞
出征的泪水
送别的人群里,龚利望酸了双眼,也没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倒是拉着她手一直舍不得放开的护士长,看出她的心思说,你妈妈来过了,带了煮好的香肠和换洗衣服,请我交给你。她说她就不送你了。
龚利的眼泪顷刻就下来了,跌落在绛红色的出行服上,洇出一连串红色的小碎花。
大年三十,疫情正紧,重庆市江津区中医院微信工作群里发出紧急通知,征集医护人员到一线抗疫。正与妈妈和妹妹吃年夜饭的龚利,沉思良久,放下饭碗对妈妈说:“我要报名。”
妹妹还小,不知道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懵懂地看着姐姐。妈妈好一阵没说话,只是机械地用筷子拨弄着盘子里的回锅肉,好一会儿才抬起头说:“我不支持你。”龚利正想解释,话还没出口,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也不反对你。”
知母莫如女。冰雪聪慧的龚利一下子就体会了妈妈内心剧烈的矛盾和在小爱和大爱之间那种艰难的选择。彼时,纵有千言万语,却汇不成一句话,龚利夹了一片蒸腊肉放到妈妈碗里。那是妈妈最爱吃的。
前不久,我微信语音采访才从隔离病房回到酒店的龚利,小心地问她,你爸爸过世,妈妈没上班,妹妹还在念初中,家里经济支柱就靠你,你有没有想过若有闪失,家里该怎么办?龚利说,疫情之下,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天天看新闻里的疫情,心里着急难过,我就是觉得我是医护人员,没有成家,也不是独生子女,即使有个万一,还有妹妹能陪妈妈。我又是重症医学科的护士,应该冲上前去。
龚利是江津区中医院出征驰援武汉的四名队员之一。同去的还有张群、曹屹和何露,都是临床护士。他们与重庆各大医院抽派的122名队员一起,组成了重庆市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于大年初九紧急出征到武汉,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12、13病区。
东院是武汉四家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这支队伍被叫作“重庆三队”。
龚利落泪的时候,呼吸科护士张群,正和来送行的丈夫依依惜别,她千嘱叮万嘱附说,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要和老人们说我去了武汉,他们会担心的。丈夫拥抱了她,使劲地点头说,你放心吧,保护好自己,我们等你回家。
进病区的忐忑
到达武汉,已是夜晚10点。接他们的大巴在城里疾驰。城市的景色依然漂亮,街灯炫彩,霓虹闪烁,只是到处都空无一人。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过来,一车人都没说话,感到了肩上压了担子。
疫情严峻,简短的休整,就到了他们上岗的时候。
男护士曹屹在微信语音里和我说起第一次进隔离病房心里的害怕时,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连声说:“你可别笑我。”用他的原话说,他是十分害怕,进入隔离病房那一刻,两条腿都在微微打颤。他努力克制着,不让别人看出来。
长得高高大大的他,是急诊科的骨干护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报名。生怕选不上,大年三十夜,他反复在电话里同护理部和医务部主任说:“我一直在急诊科工作,参与救治过的病员无数,还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我有一线救治经验,又是男生,派我去吧,一定要派我去。”
上岗前反复严格穿脱防护服的训练考核,以及负责感控培训考核的老师严肃的告诫,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新冠病毒强大的感染性,同时也多了一份担心和害怕。
虽然是个男护士,曹屹也不例外,即将进入隔离病区的他,想起了女儿可爱的小脸,她刚学会叫爸爸;想起了离家时爸妈蹙紧的眉头和担忧的眼神……
曹屹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支援武汉的一线护士,任务很明确。进入隔离病区,为病人输液、打针、护理、监测、翻身、喂饭、擦洗、处理大小便……隔离病区不允许家属陪伴,几乎所有的治疗和生活护理,都落在护士身上。与感染者绝对密切接触,稍有不慎,就可能感染。
“可是,就像战士上了战场,怎么能遇到危险就往回跑呢。所有队员,没有人把害怕表现出来,我也是,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心,就迈进了隔离病房,那里有重症患者等着我们救治呢。”曹屹说这话时,口气很特别,欣慰里透着自豪。
隔离病房里的“大白”
进入隔离病房,没有半个小时小心翼翼的准备是不行的。为了防止密切接触患者被感染,每一个进入的队员,都得在感控专业老师的监控指导下,一层一层穿防护服。12道程序,一道都不能少,还不能马虎。
等全副武装好了,他们就成了“大白”——白衣白裤白帽,全身裹在防护服里,鼓鼓囊囊的,瘦小的人也增大了一圈。病人看不到队员的脸,分不清谁是谁,在他们眼里,每个队员都是一样的“大白”。唯一能辨认的是声音。
有一段时间,张群的声音成了她负责的隔离病房病人追逐的声音。因为她总能“一针见血”。
戴着双层手套,护目镜和面屏,穿着防护服,加上汗水雾蒙了视线,平日熟悉不过的静脉输血和抽血,在这里也成了难事。好在张群善于琢磨,不久就掌握了要领。
这天早晨,她要抽22个病人的血样,给病人输上液才能下夜班。1床是位大叔,动脉采血。张群找到他的桡动脉,消毒、进针、采血、棉签按压。大叔看到按压,以为没抽到,很理解地说:“一次没抽到没关系,今天不疼,换一边再抽。”张群把抽到的血拿给他看,大叔惊喜地竖起大拇指说:“你真厉害,一针见血还不疼,技术真棒!你叫张群?我记住了,下次你还给我抽。”张群连连点头,“只要我上班,一定来……”
到了39床,一位大爷,最后一个抽血。张群在床旁做抽血准备时,大爷说话了:“你是张群对不对,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张群连忙说:“是我是我,大爷我又来给你抽血了。”大爷伸出手臂:“好好好,一针见血的重庆妹妹。”
这时的张群,穿着笨重的防护服,已经不停地工作了4个多小时,汗水浸湿了后背。
她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一忙就到了早上8点,就在我交班准备出隔离病房的时候,一位阿姨着急地叫住我,说她的血管不好找,非要我给她输上液再走,我只好返身回来,给她扎上了针。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一个病房的患者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很累,很饿,背心发冷,但那些竖起的大拇指就像兴奋剂,让我就像读书考了一百分那样高兴,瞬间有了精气神。
出隔离病房的程序36道,洗手16次,为的是不把病毒带出去。
当张群终于穿上自己的衣服坐上回酒店的班车时,感觉快要虚脱了。她摸出手机,用洗得发白起皱的手点开图库,看和女儿视频的截图。图上,女儿小脸歪向一边不看她。两岁多的孩子已经懂得亲疏,一个多月没抱过女儿,生分了。
“可是我无时无刻不想她。”张群说。
与张群有同感的是何露。这个26岁的ICU护士,当初报名时就遭到了丈夫的反对:“柚子还这么小,你要是有个什么,我和柚子咋办?”何露给丈夫看了医院的工作微信群说,“你看,大家都踊跃报名上一线,我的专业正好符合,我不上谁上。你放心好了,我会保护好自己,不会有事的,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事的。”经不住何露的软磨硬泡,丈夫不再反对。但是那晚,平时一挨枕头就沉沉睡去的丈夫,翻了一夜的身。
何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丈夫的愧疚。她说,他是老实人,是好人。
我理解她说“好人”的深层次含义。这次疫情,每个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的背后都是这样的“好人”。
何露爱柚子,想柚子,想到骨子里去了。每次视频,女儿乖巧地喊妈妈抱抱,抱不到也不哭不闹,只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静静地看着手机里的妈妈,这让何露越发觉得柚子可怜,越发想念。
有一次,换好防护服进隔离病房前,抑制不住思念的何露,让感控监督老师帮着在防护服后背写了几个字:柚子妹妹,妈妈想你了!何露说,写上了这几个字,就好像把幺妹背在了背上,心里踏实多了。
何露没想到的是,她的柚子,成了她为很多患者做心理护理的“武器”。
何露不敢说她第一次进隔离病房时看到的景象,一说就哽咽。病房安静得出奇。亲属无法陪伴,疾病的折磨,对病毒的恐惧,病友的离去,使他们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只是机械地接受治疗。
作为天天接触患者的护士,何露知道消极情绪对病情的影响。稍微熟悉病区的环境和工作流程,工作开始得心应手后,何露和她的同事们治疗之余就开始了心理护理。
说白了,心理护理主要靠和病人保持密切关系,通过倾听、开导、启迪来调整患者心理状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这,需要爱心、耐心和技巧。
何露给一个重症患者喂饭时,那阿姨总说不想吃,吃不下,情绪很不好。何露没放弃,一空下来,就找阿姨聊天,但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得知阿姨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时,何露来了灵感。她给阿姨看女儿柚子的视频,说柚子的种种萌态和可爱,说自己也想女儿,想早点把大家都治好,早点回家。触景生情,阿姨也想起了自己可爱的小孙女,她把小孙女的视频给何露看,还说,小孙女下个月就满两岁了,自己一定好好吃饭,配合治疗,战胜病魔,回家给小孙女过生日。
后来,给患者讲女儿小柚子,成了何露心理护理时屡试不爽的敲门砖。患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看到小生命的萌态中苏醒。
重症隔离病房虽然依然避免不了生死离别,但在何露和她的同事们的精心治疗和心理护理下,这里有了变化。患者从对医护没有任何要求,到主动问病情,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出院,主动和护士们聊天,学着说重庆话和他们认老乡。老病人也会主动帮助新病人去除思想包袱,有的病人还开玩笑说,每天要看到“大白”心里才踏实。
有一次聊天中,25床的一位大爷羞涩地说想要吃水果,当班的龚利和何露就记在了心上。第二天,她们从酒店里带上了自己的两箱哈密瓜,搬到病房,分给患者们吃,自己一个也没留。
龚利用这样的语言和我说当时的感受:我们把哈密瓜削好,分送到他们床前,看到他们感激的眼神,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不是护患,就是亲人,他们吃着哈密瓜的样子,是我们心里最温暖的样子。
难以讲完的故事
清代诗人袁牧写了一首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采访重庆三队的这四位来自江津区中医院的一线抗疫队员时,脑子里经常浮出的是这首小诗和苔花微小而青春饱满的样子。
我问何露,你以前在单位出过远差吗?她说没有。我开玩笑说,第一次出差就成了出征,挺有意义的。她说是。然后象个孩子似的开心起来说,在武汉,我第一次看到了雪!
一岁孩子的妈妈,其实就是个孩子呢。只不过,穿上了那身白衣,就成了战士。那天早晨从病区下夜班出来,坐车回酒店的路上,她看到了车窗外皑皑的白雪,铺天盖地,银装素裹,竟高兴地跳了起来,完全忘了饥肠辘辘和身体疲惫。她用手机照下了武汉的雪景,发给丈夫说,给咱们的柚子妹妹看雪。
曹屹这个出征之前被同事赋予保护女队员使命的男护士,自嘲地说自己没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的话语里,满是对同事的歉意和对患者付出获得肯定的自豪。
他还清楚地记得好几个出院患者的名字。12病区的于双英(音)是个教师,出院时,拉着曹屹合了影:“你为我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会记得一辈子,感谢重庆三队,感谢小曹,国家有你们真好!”13病区的陈颖(音)是个医生,出院时拉着小曹的手说:“小哥哥,感谢你,我会记住你。”
一位80多岁的退伍军人大爷,临出院时激动地把“大白”们叫到一起说,“孩子们,你们也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人。这些天,你们护佑着我,我这个老军人给你们敬礼了。说完,颤巍巍地伸出右手,敬了个军礼。”
曹屹说,那一刻,他眼里含了泪花,再苦再累都值了。
在病区里,曹屹一直是患者们口中的“小哥哥”。小哥哥不仅高大,长得也很帅,只是那些被他治疗护理过的患者,那些对他心存感激的出院者,都没有机会看到他裹在防护面罩里的模样。那是真的阳光美好。
提起那次紧急搬运氧气瓶的事,瘦小的龚利说,没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大的气力。那天,病房住满了重症患者,病房突然氧气压力不够,而病人又急需供氧,怎么办?马上去搬氧气瓶!30个应急的蓝色钢化氧气瓶,每个都重达70多公斤,比龚利还高,还重。现场没有推车,当班的6个护士就进行搬运接力。清洁区,缓冲一、缓冲二……硬是使出吃奶的劲儿,把30个氧气瓶在很短时间内,搬进了隔离病房。搬完最后一个氧气瓶,龚利浑身汗如雨下,差点瘫倒在地。
我对他们的采访是断断续续的。忙碌的他们只能在休息时给我留言或语音。我知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他们的每一个故事,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感动和激励更多的人。可是,我不忍心再占用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太累了。
这群最基层、最普通的医务人员,他们没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豪言壮语,但细微之中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震撼。
隔离病房里的“大白”,他们像一粒粒苔花,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盛开出最美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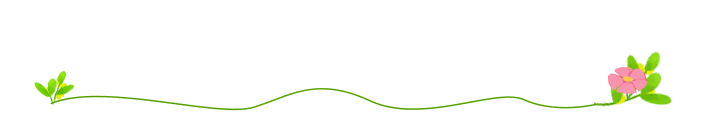
上期精彩回顾》》》
战“疫”有我 重庆作家在行动(七十三)李燕燕:退役不褪色 军装永着心

渝公网安备:500103020027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