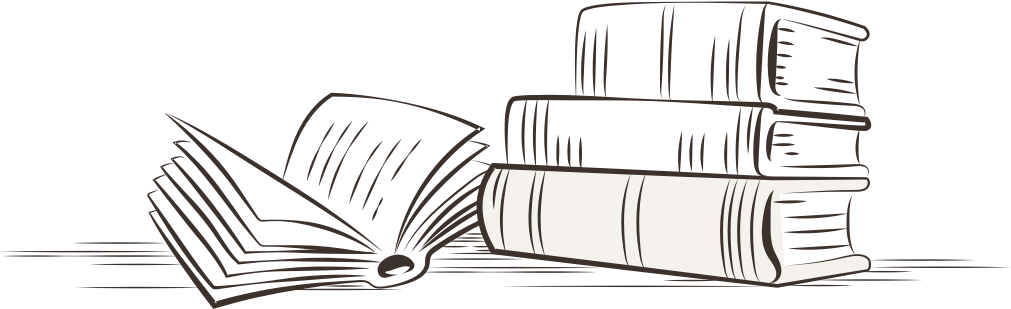岁月匆匆,1989年毕业便离开重庆师大,转眼已是二十九年,世事沧桑,我与母校也渐行渐远。但在我记忆里,还留存着一片森林---母校足球场边的夹竹桃。到了春天,它们争相长出蓊郁滴翠的叶子,盛开一树树艳若桃李的鲜花,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景致。
2017年12月15日,母校文学刊物《嘉陵潮》的编辑任中秋给我打来电话,拟采用我的短篇小说《三星月的女人》,我们就定下了会面的时间。2018年3月17日早上8点,我从江北黄泥塝出发,地铁在跨越嘉陵江大桥时,我透过车窗,望见碧蓝的江水,回味着与同学们在江边野炊的往事,也想到很快见到久违的《嘉陵潮》杂志,心头甚至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九时左右,我走出了沙坪坝地铁站台,见时间尚早,便步行到了重师老校区。远远地看见熟悉的校门,看见在方形柱上郭沫若先生题写的“重庆师范大学”几个红色大字,这就是天成路12号,我熟悉的母校。我的眼睛顿时有些湿润,不自觉地加快脚步。
进到校园,并无保安人员阻拦,却在离大门不到一百米的大楼前,摆放着一顶帐篷,两个物业服务员,在收停车费。我心里很纳闷,这些人为何不守护校门却守车库?我悻悻地回头,猛然间发现,校门在四周高大的城市建筑里,显得格外渺小,与从前鹤立鸡群的雄壮宽阔,有着巨大落差。这个曾经让我心潮澎湃的标志性大门,此时,倒像一位蜷缩大都市一隅、步履蹒跚却倔强地活着的老人,有些不合时宜,有些凄凉。原来,母校正在搬迁,新校区建在虎溪大学城。
在中文系的办公楼前,我驻足徘徊很久。“中文系”,母校响当当的专业,响当当的名字。遥想当年,我们都怀揣着《彷徨》《呐喊》,在这栋小楼进出,“愤青”似乎成为我们的代名词。而此时,我看见的中文系楼墙上,虽然校训“厚德、笃学、砺志、创新”醒目,却已满是灰尘蛛网,有的墙面脱落,明显破旧,毫无格调与情调。但我仍然能触摸到那段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
经过“男生二舍”时,我想到的是母校的大寝室、大厕所、大教室和大食堂。这栋六层学生公寓就是大寝室,虽然留下岁月的屐痕,却保持着他古朴的本色,这就是我曾经居住了四年的宿舍。在这栋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砖混房里,我们十几个同学曾挤在一间屋子,没有空调,一层楼共用一个大厕所兼浴室。多数同学穷得除了一大叠书籍外,只剩棉被和可怜的几件换洗衣物。但我们很快乐,在这里,我们拥有过从乡村到城市的第一次惊喜,有过彻夜不眠侃大山的畅快,还有偶尔邀请女生到寝室逗留一下的惬意。“男生二舍”,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无法撼动和抹去。
嘉陵潮文学社,师大中文系学子的魂。2013年,为了向母校60华诞献礼,1980-1989级中文系的学生们自发投稿,陈修元先生编辑出版了《人生突围---八十年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一书,书中也碎片似的记载了嘉陵潮文学社。我于1985年10月考进母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作家的梦驱使我加入到了嘉陵潮文学社。这个文学社成员主要是中文系学生,创办了《嘉陵潮》,追求纯文学的校园刊物。我还依稀记得,1984级的学长袁勤华,用蜡纸钢板刻印出诗歌、散文汇集的报纸,然后奔走相告,分送各系,甚至像电影中的报童一样到街上叫卖。而嘉陵潮文学社那间编辑部兼油印的办公室,磁石一般,吸引着中文系的天之骄子们。在我看来,它就是时代的《挺进报》。
我坐到足球场边的黄葛树下,企图搜索一下母校在大脑里遁迹已久的信息。校门口的那条大道,是嘉陵潮文学社开辟的“文学之角”“演讲之角”,常常聚集着一群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的年轻人。而这偌大的足球场边,原来是植满夹竹桃的,茂盛的树冠,俨然一片神秘的大森林。而喜欢钻这片森林的大学生,多少都会有点故事。现在则是一排整整齐齐的黄葛树,稀疏的枝丫,颀长树干,光秃秃生冷的石阶,一览无余。没有了遮掩,估计也就没有了故事。
就在这片森林里走出一届又一届的师范生,就在这片森林里,诞生了莫怀戚、罗伟章等一批优秀作家,有的还活跃于当今的文坛。
中午十一点,我准时到达三峡广场的金翠河,嘉陵潮文学社倪鹏、任中秋、张鹏相约见面的地方。我从任中秋手里接过《嘉陵潮》的那一刻,心突然地颤抖,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翻阅起来。二十九年了,我们分别得太久太久。我和倪鹏三位年轻编辑虽素未谋面,但彼此没有陌生感,没有代沟,因为我们是校友,是文青,同属嘉陵潮人。我们谈校园文学的困惑,谈嘉陵潮的未来,当谈到现代大学生的激情时,他们显得有些灰心失意,眼光中流露出怅惘。但我却在那三张略显稚嫩的焦虑的脸上,读到并未泯灭的希望。母校的莘莘学子,依然如我梦中的那片森林,正吐露新芽,释放出春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