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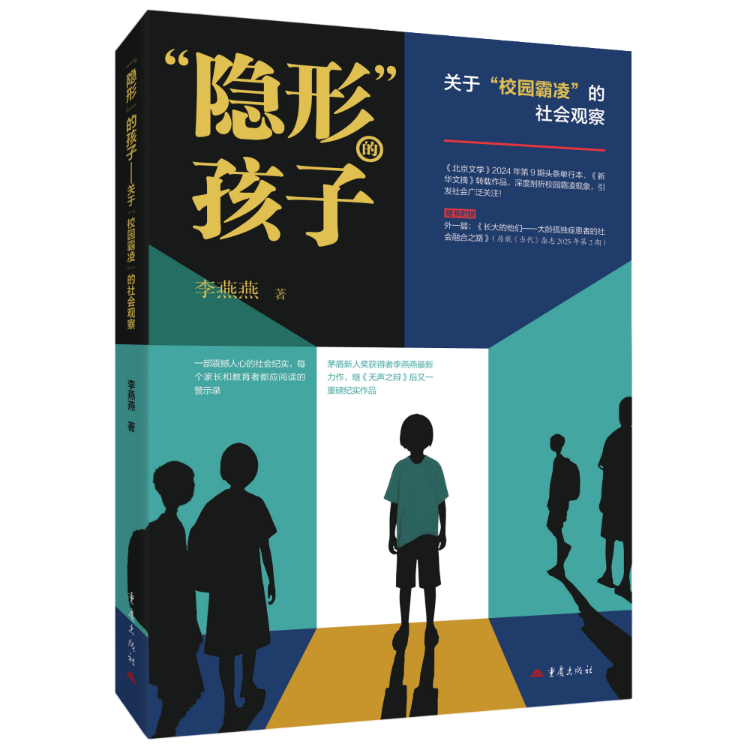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隐形”的孩子》这个报告文学单行本由主线作品《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北京文学》2024年9期刊发时原名)和“外一篇”《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当代》2025年2期)组成。大家都知道,“外一篇”这样的说法,常见于诗歌和散文,虽然书写事物各不相同,但必定有内在深层次的联系。是的,受到校园霸凌的人群,与我所采访到的大部分大龄孤独症患者,都属于青少年群体,这是第一个联系;第二个联系,两个作品有着诸多机缘巧合的“互文”现象,比如,受到校园霸凌的孩子里,常常有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同样,《长大的他们》中也有相关案例和描述;第三个联系,就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无论是被霸凌的孩子,还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在社会里很大程度都是“隐形的”,不论“隐形”的原因如何。
这本图书,本就是《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的图书单行本,原来的主标题也是《校园之殇》,因为这样的标题看起来偏“悲哀”了一点,根据出版部门的建议,要换一个主标题。《校园之殇》的开篇引言就是埃洛伊·莫尔诺《隐形人》里的一段经典话语:
一切都是从那群恶魔开始的。
你们成年人跟我们说不存在,只是为了不让我们害怕,但是你们也知道恶魔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这样说吧,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还是正常人,明天就变成恶魔了,连你也不例外。被恶魔盯上后的某一天,我竟然拥有了超能力。我可以跑得飞快,可以在水下呼吸,还和龙一起飞翔。我甚至学会了隐身。我没发疯,我说的都是真的。
埃洛伊·莫尔诺的《隐形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关于“校园霸凌”的小说。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是了,那这个单行本就叫做《“隐形”的孩子》吧。”这个题目,也刚好因为明里暗里将两篇报告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成了很合适的一个图书主标题。
先说说《“隐形”的孩子——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这个主线作品。
2023年11月,我与律师朋友孙晓云一块吃饭闲聊,她说起她正在做的一些与“校园霸凌”相关的“网络暴力”案子,我们都是母亲,共同感叹“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她鼓励我,“要不写一写与校园霸凌相关的?”我一口答应,并且很快开始做大纲。事有凑巧,《北京文学》师力斌老师也非常想要做一个关于“校园霸凌”的报告文学,但他的观点是要首先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蕴含“未成年人犯罪”可能的“校园霸凌”——是的,“校园霸凌”是社会热点,至少每一个家里有孩子的父母都会特别关心。近年来,相关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不少,《少年的你》《第二十条》等皆引人关注,但直接书写现实的报告文学还几乎未写到这样的题材。师主编非常关心这个题材的进展,常常与我电话交流他对于“校园霸凌”的一些观点和感受。我还记得,一次他打来电话,我站在马路边的树下跟他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结束时我的身上落满了黑色的小虫子。
随着采写的深入,一些曾被刻意忘记的往事渐渐浮现于我的头脑,就如,我也曾是个校园霸凌的受害者。长大的我,会刻意忘记曾经历过的伤害,但潜意识深埋处,一些心理创伤不知不觉地跟随。比如,不会说“不”,试图讨好别人求得别人善待自己,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在遭遇到更大的变故之后,渐渐消失。从心理学上,也佐证了为什么我接触到这个题材会格外兴奋。更重要的是,恶劣的“校园霸凌”事件不断发生,不断浮出水面,不断被媒体曝光,但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沉没在水下,隐私与创伤共同构成了不可见的悲伤故事——就如因为被校霸欺凌毁去名声漂泊异乡的年轻女孩,就像因为长期遭受团伙欺凌而患上重度抑郁症的少年……告诉我可以采访她的女孩已经鼓足了最大的勇气,然而我临走时,她却再三叮嘱我:“我的名字,不要写出来,不要让我更多的熟人知道。”被霸凌者的化名之下,我分明记得那一张张稚嫩却情绪复杂的脸,恐惧、自卑、难过等等皆有。也就在我的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2024年3月,“邯郸三少年杀人埋尸案”发生了——
那个血色的下午,废弃的蔬菜大棚里,三个农村少年已然被恶念烧红了双眼,他们挥动着铁铲,一下接一下,朝另一名少年狠狠打去,鲜血,惨叫,狞笑,哀告……或许,被害者此刻的哀告,越发激起了施害者骨子里的暴烈和残忍!最后,面目破碎、了无生气的被害者被掩埋在了这个大棚里……直到民警拿着微信转账记录找到三个恶魔,血腥暴虐的凶案事实才渐渐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社会大众的一个共识是:这起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案,虽然发生在校外,但种种事实却证明,这就是校园霸凌的延续,并且是极端的表现形式。

李燕燕为读者签名 精典书店供图
这就是我手头要写的这篇报告文学的最震撼人心的序章!当时《北京文学》的主标题《校园之殇》也就是这样而来。悲痛已极,愤怒已极!如此极端的恶性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与此紧密关联的公众话题“校园霸凌”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
邯郸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件发生后,在数个家长群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记得,上一轮热议,是在一个女孩被几个女同学围堵着扇耳光的视频流传开时。与后者引发的愤慨相比,前者更令家长们陷入深深的惊恐和焦虑当中。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可能24小时陪伴在孩子身边呀!
正如有人在知乎发言:“看了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我决定把孩子当反派养。”某个家长群里,有一位母亲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我告诉儿子,假如有人主动招惹你,他打你一下,你就狠狠还他两下。”
这里也引出一连串严肃的问题:校园里花朵般的未成年人为何化身恶魔?校园霸凌应当如何纳入法律层面?
后续我又关注了近年来的多个重要案例,并深入采访数起“校园霸凌”事件相关当事人以及法律、心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也要感谢另一部报告文学《师范生》的持续采访为我提供了某些便利。事实上,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者而言,题材与题材之间,本身也是存在“互文”关系的。针对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等,我尽力做出详尽探究,并在作品中给出了建议和呼吁。
关于“邯郸三少年杀人埋尸案”,大家都知道一个结果:经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最终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这样的结果,社会上众说纷纭。但我始终同意一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本质不是为了惩罚,而在于挽救。”同样,对今天诸多涉罪未成年人而言,惩罚的终极目的不是单单惩罚,应当是纠正,是救赎。对于受害者,更应全力保护、弥合伤痛。防治“校园霸凌”在路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在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2023年11月,我向《当代》交出了这个单行本的“外一篇”《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第三稿。这是我观察采访和谋划长达十几年的选题。2023年初夏来临时,我写了一稿,徐主编在亲自与我交流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又给我推荐了六七本与孤独症研究有关的专业书籍,让我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扩大视野、然后再补充采访。这样一直修改了两稿,渐渐成形。2024年,我又在徐主编的亲自指导下修改了一年,直到2025年初才定稿。其间,我也曾多次感觉修改,尤其是补充采访和结构变动太困难,几乎无法坚持下去,但最终我还是咬牙挺了过去。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其实真正的快乐并非发表出版,更在于达到了写作的既定目标,就像长跑终于到了终点。所以,可以这样总结,2024年,我写作了《校园之殇》,修改了《长大的他们》,修改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师范生》。《校园之殇》和《长大的他们》,2024年重要的两个报告文学,本就有机缘聚合到一个单行本里的。
校园霸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孤独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亦在我身边。
张国华曾是我的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他的孩子小静七八岁的时候,张国华夫妻俩带着他到我家做客。那时,无论我对他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要么喃喃自语,要么自顾自玩着手里的东西——一个橘子,或者一支笔。不一会,客厅里便没了小男孩的踪迹,午饭时间快到了,我们挨着房间找他。在主卧,小静正站在飘窗上,看向不远处的一片人工湖。我家在7楼,天气晴好,此刻窗门大开,且没有加装防护栏,窗棂刚过孩子的半身……有风徐徐吹来,静谧之间,险象环生。张国华轻柔地呼唤孩子,片刻孩子回过头,拍拍手,笑嘻嘻地跳下飘窗。咚,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地。多年后,再见小静,我会记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洞开的窗户边站着的那个小孩子,以及张国华和爱人王老师不曾言语的艰辛。这次发布会,我也曾邀约张老师来到现场。

7月13日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 精典书店供图
我与小安爸爸是文友,起先我并不知道他有一个孤独症孩子。在数年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中,他第一次向我谈及他的儿子,他说长大成人的儿子在特教班经过一系列专业训练后,在某个图书馆上班,其间有人想问更细致的东西,小安爸爸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如果真是“伤疤”,还是不能轻易去碰触。所以,我没有像约其他家长一样,专门和他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谈,而是把访谈的地点放在了一个偶然碰面的会议场合。一番对话之后,我发觉一些担心只是猜测,因为一个父亲讲到自己儿子时的那种开心、酸楚或者极其细微的欣慰,都无法掺入任何杂质。
小安爸爸对我说:“我家小安真不错,至少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说到这里,我能得见一个父亲眼里别样的神采。他的孤独症孩子,能够自己乘轨道交通列车上班,会用电饭煲煮饭,甚至会炒鸡蛋,做一些简单的小菜,做父亲的人好开心。
谢谢小安爸爸,让我体会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真诚又最可怜的父母之心。
我也记得,在浓郁奶香味的包裹下,我和唐毅面对面坐在房间狭窄的过道上。同孤独症孩子一起经年“战斗”的她,像一个专业医生一般,通俗化地向我介绍她所认知的孤独症,理性而坚强。
虽然,幼时的“来自星星的孩子”深受社会瞩目,但长大的他们,如何就业、如何养老如何被社会接纳,却因为各种因素有些“不被看见”。是的,无论是被霸凌的孩子,还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在社会里很大程度都是“隐形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想要他们“被看见”。
“我期待有朝一日社会能够完全接纳我的儿子。”小安爸爸说。
“不能仅仅依靠外界的帮助,我们自己必须自救!”唐毅说。
大多数的妈妈,都有着这样朴素的愿望:“我要在我走之前,为孩子找一个稳定的寄养机构,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监护机构,一个可靠的信托机构。”
与一位熟识的编辑聊起《长大的他们》的采访和创作,她好奇地问我,那你的作品里要介绍什么行之有效的推广经验呢?我说,这个尚在探索之中,重点是要展现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现实:困难、互助、期盼、搏击……这就是现实——在我国,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越来越被社会关注,社会保障和救助工作也在逐步完善,但康复、教育、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等几个重要环节中,现实需求与社会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很突出。
她问:“那这样的创作意义何在呢?”
我回答:“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大龄特殊群体,真正的共情一定是建立在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的社会,有义务有责任提供多元化、高质量服务,并且能够覆盖孤独症群体全生命周期,让‘来自星星的孩子’不再害怕‘长大’。”
有人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写报告文学?叙事文体中,小说才是主流呀!”有人开着玩笑告诉我,写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的,属于“末流文人”。我也看到,因为各种原因,报告文学的发表在当下比较困难。然而,我的认知是,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也是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或者说非虚构写作者的信心和勇气!今天,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除了“主题创作”,还有“民生百态”“社会万象”……在我看来,作家不仅要赞颂美好,更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
感谢《北京文学》和《当代》对报告文学对“非虚构”的大力支持!感谢刊物对于百姓关切的现实问题的关注!
感谢所有鼓起勇气用事实呼唤的受访者!
感谢所有评论者:《文艺报》原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老师在《校园之殇》发表的第一时间剖析了作品中的“伤”与“痛”;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著名评论家张陵老师为《长大的他们》撰写了关于“权益与保护”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区作协主席刘清泉老师,是的,他就是《长大的他们》中的“小安爸爸”,既是受访者、也是转发量很大的评论文章的写作者,谢谢他的担当和勇气!感谢程华老师在《法治周末》发表的锐评,感谢重师的杨华丽老师,感谢所有热心读者。
希望“隐形”的孩子从此能被看见,从此不再隐形,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李燕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

渝公网安备:50010302002751号